格奥尔基耶娃认为,复苏正在来临,但复苏将是局部且不均衡的,若要取得成功,各方必须共同行动,进行
疫苗合作和维持经济支持政策。
本文是月度系列文章“经济学家访谈”之一,英国《
金融 时报》顶级评论员对话著名经济学家讨论新冠疫情下的经济复苏
2020年将因为大萧条后最严重的衰退而被人铭记。去年夏天的增长复苏苗头被第二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(COVID-19,即2019冠状病毒病)疫情破坏,其中低收入国家受到的经济冲击最为严重——尽管疫情本身对贫富一视同仁。
由于疫苗的成功前景和重建全球经济、阻止破坏性余震的广泛政治共识,人们预计2021年会是复苏之年。国际
货币基金 组织(IMF)处于这一努力的中心——它是国际机构当中最重要的金融政策制定者之一。
作为IMF总裁,克里斯塔利娜•格奥尔基耶娃(Kristalina Georgieva)在整个新冠危机期间一直在监测世界经济的脉搏,发现问题后及早发出信号,以便能够解决问题,特别是针对脆弱国家和新兴市场。
她传达的信息很乐观,但也很谨慎——“疫苗很好,但它们不是魔杖,”她警告说。复苏正在来临,但它将是局部且不均衡的。若要取得成功,各方必须“共同行动”,用果断和统一的行动来支持复苏。这种合作可能使2021年世界经济增长率达到5.2%,远高于IMF预计的去年增长率:-4.4%。
在接受英国《金融时报》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•沃尔夫(Martin Wolf)的采访时,这位保加利亚经济学家表示,持久摆脱新冠卫生危机取决于两件事。首先,不要过早地撤回政策支持,而要在需要的地方注入刺激。其次,确保疫苗在所有地方都能尽快接种。她指出:“拥有疫苗并不等同于普遍接种疫苗。”
新的刺激措施可能预示着气候经济将迎来“变革性”的一年,也预示着在创造就业这个紧迫问题上的投资也将迎来新机会——特别是在数字技能产业。但收紧有关非
银行金融中介机构的政策至关重要,迅速采取行动重组债务、尽量减少破产也是如此。现在企业和政府的借债环境都很宽松,这意味着我们在经济复苏中需要“激励良好行为”。
从积极的方面来看,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,IMF拥有1万亿美元的额外火力,而IMF迄今已在这场疫情中调用了1020亿美元。但格奥尔基耶娃表示,她特别担心的是游说:“不要碰我的银行。是的,它很脆弱,不要碰它。”
沃尔夫:2020年我们经历了最不寻常的跌宕起伏之旅,这是难以置信的一年。我感到乐观情绪又回来了。人们开始认为,也许我们能在2021年控制住疫情,然后经济就会复苏。你怎么看?
格奥尔基耶娃:我们预计(2020年经济增长率)是-4.4%,大约是这个数字。在经历了上半年的毁灭性打击后,我们在第三季度得到了一些好消息。但随后,我们在许多地方遭遇了第二波冲击,复苏的苗头又被冰雪覆盖。
我们步入2021年的时候,复苏势头正在减弱,但疫苗的成功前景奠定了我们2021年预测的基础——这会是不均衡复苏的一年。尽管如此,至少会有复苏。
我们预计2021年的经济增长率为5.2%,这基于一个假设,即这一年我们确实能持久摆脱卫生危机。有了疫苗,这种情况似乎更有可能。
但让我说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。疫苗很好,但它们不是魔杖。在全世界接种疫苗需要时间,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想给2021年传递两条主要讯息。
首先,不要过早地撤回政策支持;拥有疫苗并不等同于普遍接种疫苗。其次,采取果断行动,让疫苗迅速普及到所有地方,普及到每个人,因为这将让我们持久地摆脱危机。
如果我们尽快普遍接种疫苗,我们从现在到2025年可以给全球产出带来9万亿美元的提振;9万亿美元,这显然是个让人无法忽视的数字。总的来说,局部、不均衡的复苏确实正在来临。我们可以通过合作和共同行动来推动复苏。
沃尔夫:在你看来,全球合作方面(尤其是疫苗合作)和维持政策支持方面(尤其是在发达国家)是否会出现政治变化?
格奥尔基耶娃:该表扬的地方我确实要表扬。去年,我们的确看到央行和金融当局之间进行了突出合作。我认为我们对于它们采取同步行动、为世界经济打下基础所做的一切认识不够。
它们的行动有助于我们IMF为低收入国家开展工作。我们将优惠融资增加了两倍,这在极端困难时期拯救了许多经济体。
尽管如此,2021年还有两个领域需要合作。第一是疫苗领域的合作。就疫苗进行合作的理由很清晰,但疫苗无法自行接种。它们需要卫生系统。要记住,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卫生系统极其脆弱,因此世界需要果断支持低收入国家。
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全球卫生系统,让人们更有韧性应对未来的冲击,因为坦白讲,这不会是唯一一场突发卫生事件。我们知道,一旦发生突发气候事件,绝对需要人们具有韧性。
第二,这场危机不会奇迹般地消除它造成的所有创伤。会留下疤痕。债务水平很高,企业债务水平很高,政府债务也很高,一旦撤销政策支持,不是每个人都能渡过这场危机。
进行全球合作以确保我们有韧性、我们留下的疤痕尽可能地少将是绝对必要的。
沃尔夫:但最终,是不是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全球性伤疤,许多国家会比我们2019年预测时预期的或希望的更穷?
去年10月,IMF自己进行了一项有趣的预测,预测显示,IMF如今对2025年的预期比一年前糟糕得多,这种糟糕不是极其糟糕或者灾难性的糟糕,而是对世界所有地区的预期都要糟糕得多。
格奥尔基耶娃:是的,当然。你看,我们要求生产者不要生产,消费者不要消费。2020年经济缩水。2021年的经济复苏也无法使我们回到2019年前的水平。
我想提醒大家,2019年的经济形势也不是非常好。生产率和增长率都低。我作为IMF总裁的第一次演讲是关于同步放缓的。我们还面临日益加剧的不平等问题和迫在眉睫的气候危机。这些问题都没有消失。
我们预计,到2025年,全球将损失28万亿美元的产出。换句话说,我们将比假如不发生这场危机穷。这就是为什么果断行动和共同行动至关重要。政策制定者的确拥有一些工具。
第一,他们可以刺激经济,使之在生产率和创造就业方面走上不同的轨道。我们如今知道数字化未来已经到来。但它并没有为每个人到来。政策制定者可以做很多事情,让更多的人和公司、让所有国家进入知识经济。这是对数字化转型和我们应该掌握的技能的宝贵投资。
第二,我们可以使2021年成为新气候经济的变革之年。气候投资可以创造大量工作岗位,而且我们也的确需要这些工作岗位。仅在
旅游业,预计就可能有1.2亿个工作岗位因新冠疫情而消失。
如果政策制定者决心投资绿色复苏,那就意味着投资基础设施建设、投资电动出行、投资再造林和红树林恢复。
沃尔夫:让我们来谈谈财政金融方面的问题。人们普遍预期,这场巨大冲击的结果是,私营部门将产生大量坏账。公司都有负债。许多国家的政府支持它们借债,这没错。但它们最终将背负巨额债务。
然后,我们不可避免地会担心金融中介机构的状况。人们原本认为银行的状况非常好。但如果借款者中出现大量坏账,势必会影响它们的资产负债表。
我们对出现债务过度积累、违约和投资受抑制等形式的余震应抱有多大的担忧?
格奥尔基耶娃:我们估计,相对于强制性资本要求,资本缺口将在2200亿美元左右。从全球金融体系的规模来看,这是可控的。因此,我们的韧性很强,但我们不能把金融稳定视为理所当然。
我想谈谈政策制定者需要全力应对的三个问题。
一是长期低利率。这是为什么我们能够背负这么多债务而未被压垮的原因。然而,利率长期处于低位本身也会产生问题,因为它会加剧风险承担。公司和政府比没有低利率时借债更轻松。这是我们最近警示的一个风险。我们发表了一篇题为《“长期低利率”与风险承担》("Low for Long" and Risk-Taking)的论文。显然,我们需要强有力的宏观审慎(政策),但我们也需要对良好行为的激励措施。
其次,低利率导致银行盈利能力下降。当银行盈利能力下降时,我们就会看到它们放贷的欲望下降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注入增长动力,因为如果不这样做的话,它们本应提供的服务将会出现问题。
第三点是你非常正确地提到的。你提到了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。它们是全球金融危机后的遗留问题。实际上,我记得去年1月我与兰迪•夸尔斯(Randy Quarles,美联储副主席)有过一次炉边谈话。我们讨论过了这个问题;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未被充分监管,施加于它们的政策也不够强有力。
去年3月,我们亲眼看到了它们状态不佳的证据。各国央行加紧采取行动,它们做了需要做的事情。不然的话,我们可能已经陷入困境。如今,金融稳定委员会(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)正在对去年3月的市场动荡进行全面评估。
已经有一些国家出现了严重的
公司债 务问题。在一些基本面薄弱的低收入国家和新兴市场,政府债务水平非常高。在某些国家,这些债务是不
可持续 的。
所以,我们的建议是什么?直面它。果断采取行动进行债务重组。在预见到会出现破产的情况下果断行动。最大限度减少破产。当出现破产时,要有相应的解决机制。
我特别担心的是游说。不要动我的银行。是的,它很脆弱,不要碰它。必须要主动出击,直面这些问题,以防它们变成大麻烦。当支持政策的力度开始减弱的时候,我们将看到这些问题浮出水面。记住沃伦•巴菲特(Warren Buffett)曾说过,当潮水退去,我们会看到谁在……
沃尔夫:裸泳。
格奥尔基耶娃:没错,裸泳。
沃尔夫:既然你一直在谈新兴市场,那我们能不能预测,将会出现一波严重的主权债务违约潮?这在一些国家已经发生了。有些地方进行了债务重组,尤其是在阿根廷。
格奥尔基耶娃:有两个国家进行了债务重组,厄瓜多尔和阿根廷。现在又有赞比亚。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要牢记。其一,许多新兴市场从此前的危机中认真吸取了教训。它们建立了强大的缓冲机制,建立了声誉很好、广受尊敬、独立的
中央银行 、监督机构和监管机构。
在此次危机中,它们都很快重新以低利率借债。一些国家采取了一些非传统的货币政策措施,而且迄今为止,我们看到市场反应是积极的。
最后,20国集团(G20)——其中包括中国——同意共同行动。它们授权IMF,为背负不可持续债务的国家制定计划,这样我们能将其债务降至可持续的水平。
沃尔夫:一切尘埃落定后,你认为我们会希望改变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相对定位吗?还是,我们实际会希望它们或多或少继续像现在这样,按照不同、但互相关联的方式做它们的工作?
如果是的,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将不得不创建一个全新的全球金融监管系统,用本质上类似的方式对待银行和非银行机构?
格奥尔基耶娃:银行和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扮演了重要角色。它们不仅互相补充,而且它们因为角色不同而扩充了选项。所以我们还未讨论是否要让一类机构吞并另一类,或者改变它们的授权。
我想赞扬IMF的同事们,托拜厄斯•艾德里安(Tobias Adrian,IMF货币与资本市场部主任)和他的团队,因为他们及早将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的问题标记为遗留问题。
收紧有关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的政策绝对是首要的。这是我们认为需要专注处理的问题。
我们需要全球系统吗?我真正看到的——在这个问题上我可能是少数派——是自从全球金融危机以来,有三个领域出现了逐步改善。其一是各国建立了强大的缓冲机制,各中央银行积累了储备。现在我们有大约11至12万亿美元的储备。
其二,我们建立了全球协调和决策的机构力量,而且金融稳定委员会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。其三,IMF进一步加强了融资能力。我们现在有1万亿美元可供调用,而且这三个因素结合起来,让我们更有韧性。
如果你去看看此次危机迄今为止的情况,是的,我们已经调用了1020亿美元。更有趣的是,82个国家从我们的支持中获益。这以前从未发生过。
但我们仍然有高达1万亿美元的资金。如果你排除之前承诺使用的资金,我们仍有7300亿美元。这说明,这套“分诊方法”让世界经济更有韧性。我认为我们需要继续巩固它。
本文根据马丁•沃尔夫对克里斯塔利娜•格奥尔基耶娃采访稿编辑而成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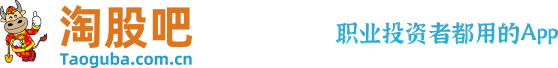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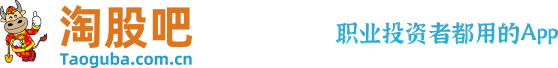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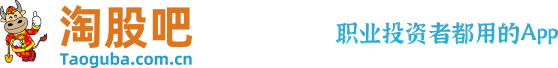
 0
0
 评论(0)
评论(0)
 收藏
收藏
 展开
展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