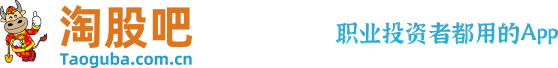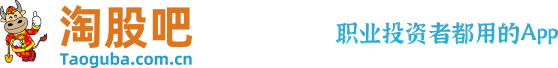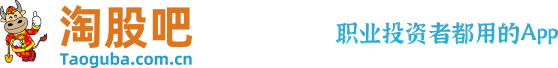96年从广州回到郴州,是因为想结束一种有漂泊感的生活。94年从铁路单位以进修的名义,从贵州兴义册亨巧马林场逃到广州武警总医院学了一年,积蓄已然花光,生活上没有了经济来源,只能去打工。到太和消化病院做了半年,夜班加麻醉,最后也觉得离自已的愿景相差太多,因而频繁跳槽,甚至到东圃一家聋哑人学校当了三个月的校医。熬不下去了,人也在江湖漂累了,就想回原位。旧同事说,原来一起在安龙指挥部的书记也调回了郴州任书记,想起在南昆铁路尾芽一号隧道时,与他多有接触,也为他的政绩做过吹鼓手(给他写过两篇豆腐块报道发到铁路内部报刊),于是想找他。心既已疲,复工复职,别无选择。那两年经常去当时最大的广州天河书城,就选了一款上等的砚盒作为礼物,去迎合文人的喜好。结果砚台被退回来了,但工作的事,他还是帮我的忙了。不过国家也在大力开发铁路建设,很多工地也已复工,正是用人之际,但我厌倦的是在铁路工地医院的漂泊生活,我要让自已稳定下来,我选择留在基地郴州。
职工医院来看病的都是单位的职工及其家属,因为时处从单位办医向社会办医的转折期,企业医院关停并转能保留下来的也是较大的国企。工作轻松,每天报到打卡,短短的看病高峰期过后,就是喝茶吹水,海阔天空。周末,如果上过夜班后休息,就跑到湘南地质队职工医院去玩,因为那里有留在郴州工作的同学李明。
这位同学的父亲原来是湘南地质队的书记,97年时已然病故。他哥接替了工作,也搞政工,办公室当个小头目。我同学临床专业毕业后就留在这当厂医了,因为文凭不硬,当年来说,能留在市里工作,与家人在一起,是相当不错的了。
26岁的人了,没有女朋友,这位同学比我还大一岁,也是光棍一条。李明的全家都炒股,他父亲走后,他妈妈炒股,他哥炒股,他也炒股。我经常傻傻的坐在他办公室听他神吹股票知识,也从那些大报小报的刊屁股里浏览股市资讯。没有智能手机,连BB机也是后来的事情。股市行情是一大厅人或坐或站地围在大墙屏幕前,紧张兴奋地盯着,发出嗡嗡的苍蝇声。不时,有个股跳涨了,或是板块逆市翻红了,就象在茅坑里被谁家小孩扔了块石头,大厅顿时炸锅了,苍蝇堆变成了马蜂窝,嗡嗡声变成了哗哇声,人们脸上有兴奋,有惊讶,有羡慕,有懊悔……这些,都是李明带我去当时泰阳证券营业大厅看到的景象。
不久,大厅里又添了好多柜台机,于是每台机前攀了一个人或两到三个各式人等,他们的手指飞快地敲打着键盘,
计算机 发出嘀嘀的声音,发现有不认识的人也凑在旁边看,就有意无意地用身体去遮挡自已的帐户或自选股。当然,经常泡在大厅里的老股民,不熟也熟了,有时会会心一笑,更多时候是后来的先打招呼,涨了吗?他们互相问候,酒逢知已。如果是新股民,则讪讪地傻笑一下,或者不好意思地走开了。也有自告奋勇当讲解员的,指点K线,激扬数字,从KDJ到MACD,从乌云盖顶到仙人指路,从芙蓉出水到断头斩……
我就是这样跟着李明去玩时,认识了陈芳的。
那天睡了懒觉。踩单车到泰阳证券门口买了两个烤红薯,用塑料袋装了,也没来得及剥了吃,就啪啪啪地登楼去找李明。天天厢混的的老同学,哪怕在花花绿绿的拥挤人群,也能一眼认出他来。我拎着烤红薯环视一圈,就在自助机前找到了他。他旁边还站着一个女孩子,穿着嫩嫩的粉色毛衣,脸上皮肤相当好看,不知是否被粉红的衣裳映得。一双大眼睛水汪汪,也是紧张兴奋地盯着屏幕。我叫了一声,明哥,早啊,我来晚了。李明头也没扭,手不停地敲着,说,你你你,你个扎崽,想要开户又不早点来……
我用肘捅了他一把,你个崽!啥时找了女朋友了,也不叫兄弟晚上出来呷杯啤酒。口吃的李明更急了,说,你个崽不要乱讲哦,这是我邻居!陈芳在一旁脸唰的红了,竟然不正视我。我也不是丑八怪,我可是迷倒一班妹子的帅哥呢,要不是没钱,早都女朋友排队了。
“她姐在这上班,一会带你克,身份证带了没?”